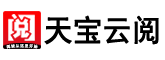又过了两天,我的腿已经结痂了,已无大碍,我就继续干我的清扫的活计,等擦到大书房的时候,福柔和我说起话来,我还以为从此她不理我了呢。
“楚彩,坐这儿,和我说会子话。”福柔说道。
我坐在她对面,看她好像比上次见我高兴了一些,由于我知道面包的事儿,他对我有所防范,她当然高兴了。
“楚彩,你进府有些日子了,怎么不见你说说你的家乡呢。你怎么会读书识字呢,你难道也是官家出身?”福柔说道。
“奴婢少年漂泊,游走四方所以见识广博,我以前的夫君就是读书人,所以耳濡目染的,也就会读书识字。”我说道,编一下吧,告诉她我是未来人她也不能信,再把我弄到宫里进行解剖,我就完了。
“那天,我失态了,你也是女人,我想你应该能理解。第二天,塔瞻在皇上面前和欧洲使者比试箭和枪的准头,塔瞻表现出色,还夺了使者的火枪呢。皇上高兴,就让专给洋人做饭的御厨做的面。。。面什么的,还赐了玫瑰露。我就让他送给你,也想让你明白我对你的好是真诚的。”福柔说道。
“福晋,你这话就见外了,我也是机缘巧合才来到府上的,认识你是我奴婢的荣幸。”我说道。心想,管你是不是真心,再跟老子玩儿锁喉,我就跟他拼命。
“你跟我回屋,我这有玫瑰露,你也尝尝。”福柔说道。
别和好吃好喝过不去呀,我就随着她去了她的屋子,屋子里有股淡淡的兰花香气,说实话福柔不坏。
她给我倒了一盅,我说道:“福晋,这是法国红酒,是不能用酒盅喝的,要用琉璃杯子,要不喝糟蹋了。”
“那听你的,红袖去,取两只琉璃杯来。”她说道。
不一会儿,红袖拿来了两只琥珀色的琉璃杯,我倒了一点,然后用手摇了摇杯中酒,在鼻子上嗅嗅,然后小口呷着,品着,说实话,在2011年我也不搞这洋玩意儿,实在是粗人一个呀。
她也学我的样子品着酒,我扫了一眼装红酒的篮子,里面还有几个干吧面包。已经长毛了。
“福晋,这红酒叫做赤霞珠,是法国红酒,要放阴凉处储存,那几个面包就扔了吧,已经坏掉了。”我说道。
“怎么能坏了呢,我还没舍得吃呢。”她有些遗憾地说道。
“额娘,馨儿也要喝红红。”馨儿是福柔的女儿,她没有儿子,有两位其他的夫人生了男孩儿。馨儿奶声奶气地说,很可爱。
“小孩子怎么能喝酒。”福柔温柔地说道。
“格格几岁了?”我逗着她。
“馨儿三岁了。”她花朵一样的小脸,真是一剂忘忧剂。
“馨儿和红袖出去玩儿去,额娘正唠嗑呢。”福柔让红袖领着她出去了。
“楚彩,我看着塔瞻好像很喜欢你,但他这人嘴硬,从不说出来。有事儿爱在心里闷着。”福柔说道。
“福晋,我不才,可以交你如何笼络他,既然你深爱着老爷,想是也每日必想着这怎么笼络他的事儿吧。”我说道。
福柔脸有些红了,默认了。
“那就从这玫瑰露开始吧,这酒在我们那儿,老毛子是晚上点上红烛,然后和心爱的人一起喝的,喝得微醉,你想怎么样不行?”我说道。
“福晋,看你喜欢丹青,诗文也不让须眉吧。”我说道。
“诗文我倒是不太擅长,大书房的书有的也没怎么读,我看你倒是时常去读。”福柔说道。
可能塔瞻这个人一介武夫也不太好这口儿。
“那就给他画画,画自己想说的话。”我说道。
“这个我倒是擅长。”福柔说道。
“听下人们说,你经常给她们讲好笑的故事,能不能也讲个给我听听。”她说道。
“好呀,福晋,这个我在行。讲一个什么呢,嗯,,,对了,我们家乡话可逗了,我就讲个笑话吧。”我说道。
“各位注意啦啊,咱这疙儿眼瞅要降温了,大家出门多注意啊,别杨了二正的到处撒磨,-跩一跤,埋了八汰的。-
工作上也别老突鲁反仗,半拉咔叽的,有点敬业精神。虽说这年头挣点钱都不容易,但也别老-买那便宜娄搜的破玩意儿,对自己好点儿。-
家里头家务活也多干点,别总整得屋里屋外皮儿片儿的,墙上也魂儿画儿的。工作一天回来看-着多闹听啊!-
性格外向的,稍微收敛点,别老跟欠儿登似的,二虎八叽,毛愣三光的,说话办事有点谱,败-总武武玄玄的瞎忽悠,武了豪疯的,时间长了,也让人咯应。-
性格内向的呢,多和人沟通,说话别老吭吃瘪肚的,做事要七拉咯嚓,麻溜儿利索儿的。-
年纪轻的呢,不要习里马哈,得得搜搜,跟老人说话客气些,有点耐心,别总鸡吃掰脸、个个-棱棱的,多和人唠嗑,别动不动就支把起来,虽然东北人都不是囊囊踹,也不能惹毛了,要不-干仗也贼讷。-
年纪大的呢,也不要脚着自己已经老天扒地,老么喀嚓眼了,要保持年轻心态。-
总之,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多上街(gai读一声)溜达溜达,别老趴家里把自己整得罗锅拔象-的,时间长了无机六瘦的!-
另外,提醒大家一句,下雪天就败出去了,省得一不小心卡到马路牙子上,再把菠萝盖卡吐露-皮了,就有你闹心的了!”
福柔听了咯咯直乐。我还解释了她听不懂的几句话的意思。
“你们这是笑什么呢?”是龟孙子。
“老爷,下朝了。”福柔说道。
“是。”塔瞻看到我也在,还是坐着和她说话的。眉头一锁,有些不高兴。
“奴婢,这就退下了。”我马上抽身逃之。
正走到醉月桥的时候,阿巴汗挡住了我的去路。
“楚姑娘,今儿好了,大家都想你呢。”他说道。
“谢大家记挂。”我说道。
“今儿,我和管事儿的说了,让你去送手巾。”他含笑说道。
我瞠目,我有瘾呀,我难道是铁匠铺里的砧子,挨打的命?
“我不去,上次都伤了腿,以后也不去了。”我说道。
“就帮帮忙吧,孩子们的屋顶还缺钱呢,求你了。”他恳求道。
“求我也没用。我不去。”我往前走。他就一直跟着。
“这次绝不摔你了。”他硬是把手中的手巾塞我手里。
倒霉死了,倒死霉了,这算什么呀,我生气。
磨磨蹭蹭地往尚武堂走,一路上过了惠亭,就听里面有人说道:“其沸如鱼目,微有声,为一沸。缘边如涌泉连珠,为二沸。滕波鼓浪,为三沸,已上水老,不可食也。”
这是侧福晋色赫图氏屋里的大丫头绮罗。看来侧福晋也不全是职业麻手,色赫图氏长得很美,但是没有福柔高贵的气质,她此时正喝着杯中茶,用眼斜瞄着我呢。我上前纳了万福。快步要走。
“听说福晋都向你请教怎么虏获男人心?你本事不小呀。”她说道。
“奴婢不敢。”我说道,我什么时候成了爱情专家了
“你这是去哪儿?”她问我。
“奴婢,这是去。。。。”我摇了摇手中的手巾。
她二人一阵笑声,“去吧,带好了腿垫子。”她说道。
我辞了她径直往尚武堂走,思忖着办法,怎么能嘲弄了他们,自己又不被嘲弄呢。